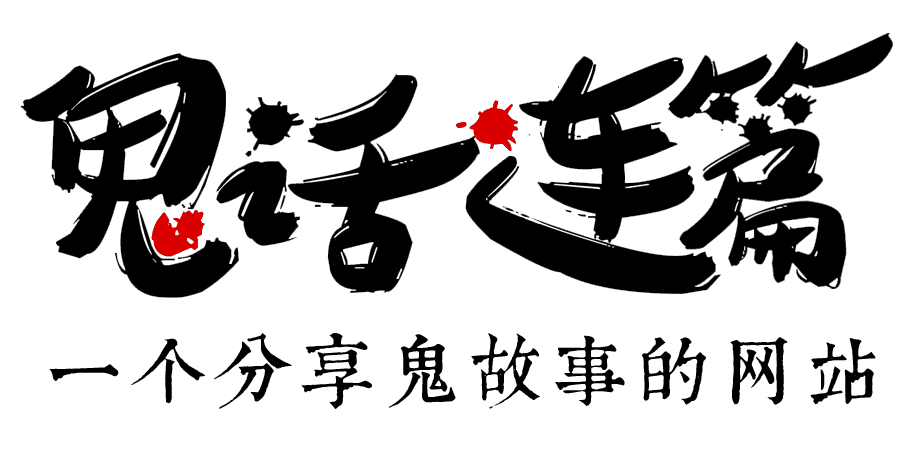1971年,又一套流行文化组合拳重塑了时代:《斯维特拜克之歌》 [22] 和《夏福特》 [23] 这两部低成本电影卖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票房。黑人剥削电影诞生了!准备好了踏浪而行的是霍洛威书屋(Holloway House),一家廉价读物出版社,1959年由两名好莱坞白人宣传专家创立。公司在1965年沃茨骚乱后猛然改变方向,因为管理层在灰烬中看见了一个缺少服务的受众群体,开始为非裔美国人读者大量生产平装本畅销书。
执掌霍洛威书屋的是海盗黑胡子的伦理精神,出版社挣得盆满钵满,旗下的标杆作家艾斯伯格·斯利姆(Iceberg Slim)和唐纳德·戈内斯(Donald Goines)只能分到一点零头。公司出版十二份杂志,其中包括《玩家》(Players )——面向非裔美国人的《花花公子》翻版,财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还在黑人解放运动中发挥讲坛功能——直到老板们认真读过一期杂志,坚持要编辑去掉所有政治文章,并且让模特看上去尽可能像白人。
约瑟夫·纳泽尔(Joseph Nazel),作家、活动家和记者,在《玩家》杂志当过一年编辑,每分每秒都对它恨之入骨。他猛灌威士忌,写字台抽屉里藏着手枪,狂暴得像龙卷风似的生产纸浆小说,作品均由霍洛威书屋出版。纳泽尔能在六周内搞出一本书, 他写了《黑色盖世太保》(Black Gestapo )之类黑人剥削电影的衍生小说和《黑色愤怒》(Black Fury )之类的硬汉纸浆小说。众所周知,他从未向其他出版社提交过书稿,奇异地忠实于最轻视其天赋的这些人。在他疯狂产出的纸浆小说之中,请看《黑色驱魔人》(The Black Exorcist )。《驱魔人》首映仅仅九个月,纳泽尔的黑人剥削版本就准备好登上书架了。
巴巴多斯·萨姆(Barbados Sam)和他的女人希拉是洛杉矶外围地区一个崇拜撒但的巫毒邪教的最高男女祭司。他们的劝诱词很简单:“该死的白人上帝和该死的白鬼子宗教他妈的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然而剧情迎来了冷笑话般的转折,这个邪教其实是黑手党的幌子,巴巴多斯·萨姆和希拉逼着真正的信徒去刺杀黑帮的敌手。萨姆和希拉的骗局就没有一英寸不是假的,直到他们杀死了教派的一名叛徒(很可能还是警方线人)。希拉的眼睛变成绿色,她被真正的撒但附体了。“现在该从收钱杀人更进一步了,现在该肆意杀戮了。”黑暗尊主充满激情地说,梦想着挑起种族战争。

《黑色驱魔人》,约瑟夫·纳泽尔著。


《地狱门房》,杰弗里·康维茨著。
他们的对手是正直的灵魂兄弟罗杰·李大人,基督重生教会的助理牧师,在发现上帝前曾是一名街头皮条客。希拉显出恶魔的分趾蹄子,企图引诱李,失败后蹲在他的《圣经》上撒尿,而他用皮带抽她赤裸的臀部,把她赶上大街。与此同时,一个想戒掉撒但崇拜恶习的年轻邪教徒把祖母扔出了医院三楼的窗户。
纳泽尔从《驱魔人》里选取段落,给它们披上粗野而肮脏的贫民窟外衣,书里有不少注水段落,例如母亲花五页篇幅号啕哀悼死去的婴儿。然而纳泽尔是一名与其所属社群有着紧密联系的非裔美国人,因此《黑色驱魔人》把握住了洛杉矶街头生活的精髓。这本小说的高潮是重要人物被乱刀当头砍死,而他控制的邪教在旁边吟唱“白色是死亡的颜色!黑色是生命和力量!”它显然很清楚该怎么将情感传递给文学市场上它小小的细分区块。

《守护者》,杰弗里·康维茨著。

《守护者》(The Guardian ) 里有大场面动作、心灵大战和出岔子的降神会,但它的变性者恐惧情节转折实在令人厌倦,因此整本书平淡得仿佛一块圣餐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