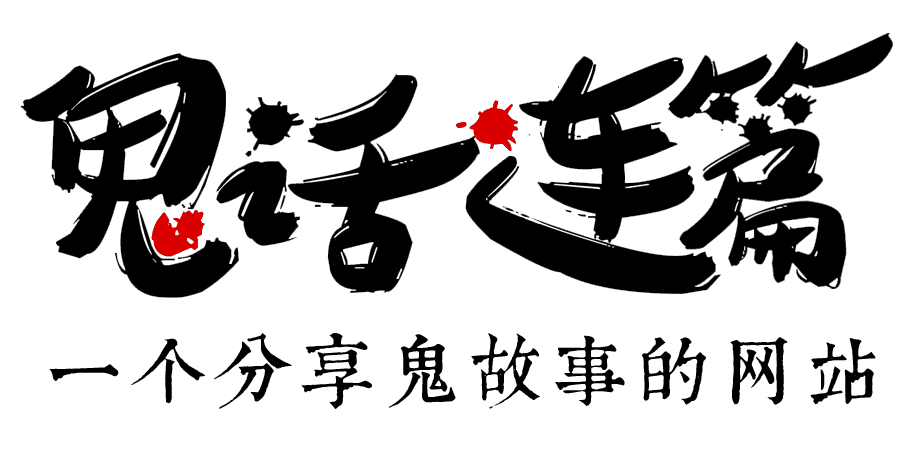这是朋克摇滚爆发的那一年:1974。这也是詹姆斯·赫伯特出版《鼠群》的那一年,两者差不多是一回事。赫伯特于2013年去世时已是英国最成功的恐怖小说作家,全世界销量高达五千四百万册。他写鬼故事或者历史和惊悚小说,但他最初的两本小说——《鼠群》和《雾》(The Fog ,1975)则是原始朋克的狂暴之作:卑劣,恶毒,反建制,低俗,直接从赫伯特的身份核心扯下一块,用他彻底而决然的信念加以弥补。斯蒂芬·金评论说赫伯特的作品有一种“原始的紧迫感”,假如“原始”指的是“去除一切掩饰”,而“紧迫感”指的是“揪住你的衣领冲你尖叫”,那么我们不得不表示同意。
前者被视为一本傻到家的小说。它写什么?老鼠。老鼠想干什么?吃人。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在为《观察家》(Observer )写的书评里称这本小说“无疑足以让啮齿类动物作呕,任何人类都只想把它扔到一旁”。然而即便在当时也没人在乎马丁·埃米斯的看法,初版的十万册不到两周就卖光了。

日后赫伯特将亲自设计小说封面,他蔑视传统,坚持使用白色背景(黑色是恐怖小说的标准背景色),用银箔和金箔的结合让出版社大惊失色。
《鼠群》,詹姆斯·赫伯特著。
小说写到第三章,鼠群吃光一条小狗,从婴儿身上撕掉血肉。书里有一段人被活活吃掉时的意识流描写。“老鼠!他的意识喊出这两个字。老鼠正在活活吃掉我!上帝啊,上帝请救救我。”鼠群唯一没吃的是哈里斯,一个行动派的男子汉。这位从不废话的东伦敦艺术教师有个不停需要拯救的女朋友,哈里森讲求实际,性格坚韧,怀疑所谓的专家。听说伦敦市在招募灭鼠人员,哈里斯冷嘲热讽。
卫生部副部长用毒气熏老鼠,鼠群消失了。问题解决了吗?没那么简单,哈里斯嗤之以鼻……老鼠狂潮卷土重来。它们掀翻地铁,吃掉形形色色的伦敦居民。只有哈里斯是它们啃不动的硬骨头,他用拳头把老鼠砸成肉泥,拯救了他的学校。新点子:超声波。哈里斯认为毒气是娘们儿的把戏,超声波愚不可及。他抄起斧头,碾过老鼠铺成的活地毯,找到了巨大的双头鼠王。“它的身体噗地爆开,像一个装满了深红色血液的巨大气球。” 故事结束。

为了证明越小越吓人,赫伯特从饥饿鼠群转向诱发疯病的细菌。
《雾》,詹姆斯·赫伯特著。
赫伯特下一本小说《雾》里的行动派主角是约翰·霍尔曼,他为环保部调查一个军方的化学武器储存地点,这时大地开裂,毒气从无底洞里喷发出来。它形成一团云雾,像致命臭屁似的飘荡在英格兰大地上,牛只精神错乱,学生阉割体育老师(赫伯特最讨厌体育老师),鸽子把人活活啄死,飞行员驾驶满载客机撞进电信塔。在全书最著名的场景之中,148820个人同时蹈海自杀。
毒气被证明是支原体这种细菌巨大化后的结果,但霍尔曼才不在乎呢,他要炸他个天翻地覆。科学家、警察和政府官员企图阻止他,但不可避免地纷纷羞红了脸。“呃,霍尔曼,看起来我们欠你一个道歉。”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太他妈对了,爱哭鬼们!伦敦陷入疯狂,霍尔曼拿切断的脑袋当球踢,开着毁灭级车辆碾过宗教狂,用机关枪扫射发狂的公共汽车司机,用炸弹挽救了局势,然后救出女朋友,发誓要让政府里的那帮混蛋统统下台。故事结束。
赫伯特交出了两部《鼠群》的续作,1979年的《巢穴》(Lair )和1984年的《领土》(Domain ),尽管都比不上原作,但老鼠还是吃掉了很多体育老师。《鼠群》(还有一定程度上的《雾》)为以后的风尚奠定了模板,因为赫伯特向恐怖小说家们揭示出两点了不起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将会引导英国恐怖小说的方向:人类很美味,英国到处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