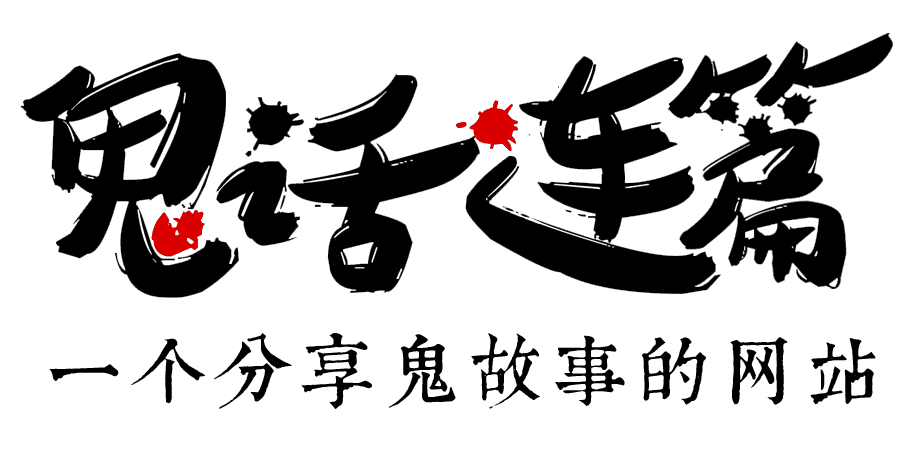当年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但看他们这样,心中也涌起一股不知该说是悲伤还是害怕的情绪。因此我不时就会跑到母亲的枕边,或是到隔壁房间那些交头接耳的亲戚身旁。
这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医师的故事。
我父亲原本是小学老师,后来被招赘到这个家来,才当上了医师。当年刚开始要求医师要有执照时,内务省特例核发了一些执照,给行医多年的家庭。于是我父亲就在我祖父过世后,直接继承衣钵,当上了医师。
父亲过世时我才七岁,所以对他的记忆只剩一些片段,但还是隐约记得一些事:他总是一脸落寞,但并不是一个不讨喜的人;他嘴边留了一点茶褐色的胡子;他非常疼我,只要他出门外宿,就会担心我有没有受伤,有没有突然生病,甚至还因此而睡不着。还有,父亲到我五六岁时,都还叫我“娃娃”——在我家乡的方言当中,“娃娃”是小婴儿的意思——据说他还常因此成为我母亲的笑柄。
“看样子,说不定这孩子到了十岁、二十岁,你都还会叫他娃娃。”当年母亲常这么说。
就因为父亲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对我母亲表现得非常体贴。这份体贴有一部分或许是出于他的赘婿身分,不过追根究底,大部分应该还是来自他那与生俱来的温厚性格。据说他也因为这样的个性,而显得非常胆小。只要有身受重伤的病人上门,我父亲就会比病人还惊恐,脸色惨白地为病人治疗。
据说有一次,有个病人腰上肿了一大块。正当我父亲战战兢兢地切开患部时,病人竟对他说:“医师,我没那么痛,请您放心大胆地切吧!”
这是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父亲死后,亲戚们觉得我母亲还年轻,又有家业要照顾,便建议她招上门的夫君,好接下医师衣钵,但母亲就是不肯。说穿了,后来医术开业考试规则很快就要正式执行,那张特例执照其实也不能再继承下去了。不过要是当时立刻招赘,至少还有一代人可以享受这样的恩惠。所幸当年我家还有点财产,不至于马上陷入困顿,所以亲戚们对再招赘的事,也就此作罢。
和父亲比起来,我母亲算是相当精明干练,个性里带着些许不服输的成分。她在我八岁那一年生了一场病,高烧不退。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伤寒之类的病吧。当时亲戚们找了一位从南方迁徙而来的山田医师看诊,他说我母亲的病很难痊愈,于是亲戚们便轮流过来照顾她。但毕竟母亲身染重病,所以大家都不敢在家里大声谈笑。亲戚们打照面时,表情俨然就像眼前有什么又黑又沉重的东西似的。当年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但看他们这样,心中也涌起一股不知该说是悲伤还是害怕的情绪。因此我不时就会跑到母亲的枕边,或是到隔壁房间那些交头接耳的亲戚身旁。
然而,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是个闷热的夜晚。原本我母亲枕边随时都会有亲戚坐着看顾,但当天亲戚却都不在。我一坐下,玄关那边就传来木屐咔啦咔啦的声响。不久之后,一位医师提着小药箱走了进来,我还以为是山田医师来了。此时,医师面向母亲枕边,也就是我的右前方坐下,把白皙的右手放在母亲的额头上轻抚,一边看着我说:“我昨晚也来过,没碰到你。”
医师用很和蔼的声音说。这个声音和说话略显含糊的山田医师不同,于是我端详了一下他的长相——这位医师的轮廓并不棱角分明,但脸庞白净,嘴边留着一点胡子。
“你这是大病,我帮你带了上等的药来,赶快吃吧。”医师说完,母亲小声地回答:“山田医师的药比较好,他的药我就愿意吃。”
我觉得母亲辜负了人家的一番好意,于是便开口说:“妈,既然医师都这样说了,您把药吃了吧。”
然而,母亲还是坚持:“我已经在吃山田医师开的药,不会再吃其他人的药。”
还把头别了过去。我很讨厌如此顽固的母亲。
“妈,别说这些傻话了。”
我讲完之后,医师看着我说:“那我把药备妥留在这里,再麻烦你喂她喝吧。把这些药喝下去,很快就会康复了。”
医师说完之后,把药箱放在腿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些药,再把药包进纸片里。行灯的光线朦胧地照在他的腿上。我好奇这位医师会开什么药,便一直盯着他看。然而,我的目光突然被医师的右手无名指吸引——他的右手无名指有点弯曲,手指的外观和包药的手势,都和我那过世的父亲如出一辙。看到那只手指之后,曾几何时,我开始觉得这位医师就是我父亲了。
“是爸爸特地送药过来。”
我心中这么想着。“往生者送药来”这么神奇的事,我竟不觉得惊恐,可见我真的是很想念父亲。
不久之后,医师已把药备好,还包成一袋,放在母亲枕边的托盘上。
“我先告辞了,药由你喂她吃就好。”
语毕,医师静静地起身,走出拉门外去了。我满脑子想着那份药,于是便随即到母亲枕边,打开药袋。
“妈,您快起来。”
听了这句话,母亲不发一语,稍微张开了嘴巴。我连忙把药送进她口中,再拿起茶杯倒了一些水。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了?”
“您吃了爸开的药。”我回答。
当天清晨,母亲的烧就退了;到了隔天傍晚,她已经可以喝粥了;两三天后,母亲就痊愈了。我说出父亲来过的事,大家都啧啧称奇。其实那天晚上,隔壁房间有三个亲戚在,但他们不仅没听见木屐声,连有人来过都不知道。只有母亲说她做了父亲出现在病榻前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