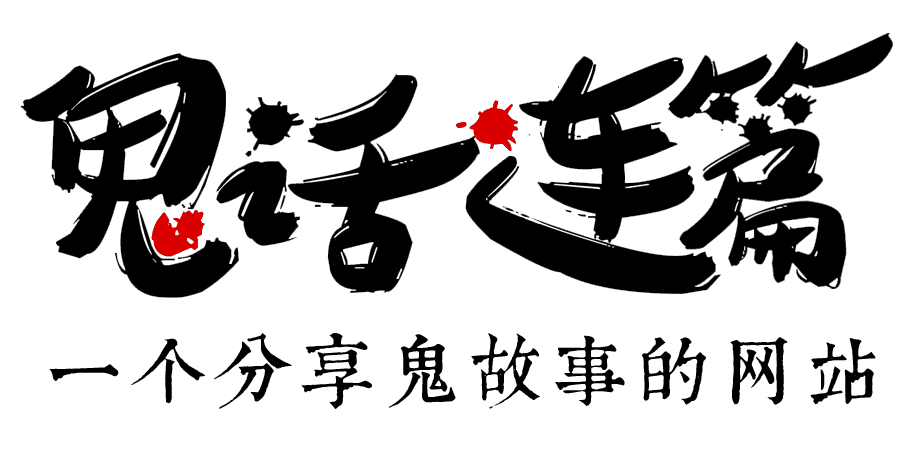唐代余干县县尉王立选官调职,在大宁里租了一处房子住。不幸的是,因为撰写文书的时候出现失误,被主管官吏申斥之后,解除官职。
他在大宁里租住甚久,手头的钱花得都差不多了,被主管部门放谴之后,又没有了经济来源,日子过得日渐窘迫。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卖掉仆人,往来代步的马匹也换成了银子,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银钱花光,终于变得穷困潦倒。堂堂的前县尉,差点与乞丐为伍。
身上没有钱,也得想办法活下去呀。听说附近的寺院每天施粥,周济穷困之人,他狠了狠心,也加入了那个端着破碗,等待薄粥的队伍。当然吃不饱,可是,也总不至于饿死。
一天晚上,他从寺院回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路往租住的房子走去。
草色烟光残照里,一行归鸿向南飞去,而他,是羁旅天涯的倦客,归乡之路却遥遥无期。想着这些,心里便浮起细细碎碎的身世之感。
正当王立长吁短叹的时候,他发现,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子,缟衣素服,身上只携了一个小包袱,相貌颇为秀丽。王立快走,她也快走,王立慢走,她也放缓脚步。或前或后,跟在他的身旁。
王立心想,这女子孤身一人,在路上独行,大概是担心遇见强人,所以有意无意地与我结伴而行,我不如同她聊上两句。于是便开口搭讪起来。
王立说话的时候,语气诚恳,那女子对他也没有什么戒备,二人意气相投,相谈甚欢。
天色渐晚,那妇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立担心她一个弱女子赶夜路,遭逢不测,因此盛情邀请她到自己家住上一晚。那女子想了想,也没有推辞,就跟着王立来到了他那个破败不堪的家。
烛影摇红,窗纸上,两个人的身影越靠越近,终于合成一个。灯灭了,万籁俱寂。
欢情总是短暂,日上三竿的时候,王立才从梦中醒来。昨夜发生的事,好像一个粉红色的梦,美丽,却不真实。也许是老天看他太可怜,才安排了这么一个美梦给他吧!上天待他也算不薄。他躺在败絮之间,嘿嘿嘿嘿地傻笑起来。
「你笑什么?」
王立闻言一惊,朝床头望去。昨夜的那个女子,端坐床头,宛然犹在。
「没……没什么?」王立结结巴巴地道,他直起身来,不敢说,自己原本以为这个女子,不过是穷愁生涯中的一个绮梦。
女子看了他一眼,也没有再追问,轻声道:
「郎君的生活,怎么困窘到了这个地步?妾身住在崇仁里,条件至少比这里强一些,你愿意跟我到那里去住吗?」
王立心里对这从天而降的女子充满了爱悦,而且,听她的口气,似是能够接济自己的生活。人财两得,这样的好事,哪儿找去。当即道:
「不瞒小娘子说,我现在穷极无聊,差点倒毙街头,你这样诚信待我,是我所不敢想的。可是,我这样身强力壮的人,都无法维持生计,你一个女人家,又靠什么谋生呢?」
白衣女子道:
「我少时嫁与商人为妻,夫亡十年,仍薄有产业。街市上的店铺,每天都有收入。早晨到店里去,晚上回家,每天总能有三百钱入账,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你授官的日期未到,若出去游历,身上又没有盘缠,倘若不嫌弃的话,可以与我同居一段时间。」
王立没有推辞,跟着这个女子,来到她位于崇仁里的家。
这女子的家里,一切都井井有条,所有的家什,丰俭得宜,看来是一个理家的好手。该花的钱,从来不省,不该花的,一文也不乱用。
虽是萍水相逢,这女子对王立却很是信重,家里的钥匙都托付给他。为人也很贤惠,每天早晨,先给王立准备好一天的饭食,然后才到店铺里去。晚上回来,又把从市场上买的米、肉、布帛等日用品和开店挣的钱交给他。每天如此,从无例外。
这女子忙完家里,又要忙家外,很是辛劳。王立看在眼里,也是大大不忍,就劝她买一个仆佣,打点家务,与此同时,也可以在生意上搭把手。可是,每次王立刚提起话头,这女子就想方设法地婉言谢绝了。见此情景,王立也不好强求,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光阴似箭,一年过去了。
选官的事仍然遥遥无期,王立在仕途上,渐渐绝了望。可是,上天在另一方面给了他补偿,他收获了一个温馨的家。这对露水夫妻,感情日益深厚,那个女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王立仍是闲居在家,一直也没有个正经营生,那女子对此却毫无怨言。
妻子出去的时候,他就留在家里,带带孩子,看着婴儿那又白又嫩的小手和小脚,心里就充满了喜悦。
高居庙堂,光宗耀祖,也不会比这更快乐吧!他想。
生下孩子不久,那女子就又开始了忙碌。每天都到店里去。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午还要回来一次,给孩子喂奶。
把那个又白又胖的娃娃抱在怀里,敞开衣襟,胖娃娃就嘎嘎笑着,欢天喜地地扑上去,咕咚咕咚地喝起奶来。
正午的阳光照进窗子,女人的肌肤白得象雪,一绺头发从她头上滑落下来,慢慢遮住了眼睛。王立从身后抽掉她头上的金钗,替她将头发挽上去,又将钗子插上。
屋子里面那么宁静,能够听到窗外叶落的声音。
又一年过去了。
孩子出落得眉目分明,十分的可爱。他已经开始蹒跚学步,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高兴的时候,龇着两颗雪白的小门牙,拍着小手笑。抱在怀里,是浓浓的乳香。仿佛,他的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乳汁。令人忍不住想在那嫩白的小脸上咬一口。
这是王立夫妻二人紧攥在手心的一块珍宝。
这个小小的婴儿,将一个落魄的男人,一个丧夫的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日子如河床里的水,一天一天,缓缓地流。
王立一直沉浸在这混沌的幸福当中。
有一天,妻子做好饭菜之后,便早早出去了。中午也没有回来。傍晚,别人家的烟囱早就冒起炊烟了,还是不见女人的影子。孩子一天没有吃奶,饿得哇哇直叫。王立心里有些焦急,抱着孩子,一遍一遍地到门口去眺望。可是,每次来到门前,都发现,没有,仍是没有。
市场早已停止交易了,妻子还没回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提心吊胆地等到半夜,才听到院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不一会儿,门开了,女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手里提着一个革囊,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意态惶恐。王立吓了一跳,这女人平时有泰山崩倒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待王立发问,女子便道:
「我有一个仇人,刻骨铭心,痛彻骨髓,这么多年披肝沥胆,一直想报仇雪恨,总也没有机会,今日,天赐良机,终于如愿以偿。」
「大仇得报,此地不宜久留,我要即刻离开京城,望君保重,今后好自为之!」
「这房子,是我自己购置的,花费五百缗,契书就在屏风里。屋子里的服玩器用,也都送给你了!」
「此后浪迹天涯,这孩子我不方便带走,他是你的骨血,望君好好待他。」
王立听了这话,宛若晴天霹雳,他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结束了。他呆立在屋子中间,半天也不能动弹。
那女子看着王立那呆若木鸡的样子,也潸然泪下,可是,不管王立如何苦苦挽留,她都不为所动,执意要走。
不过一天的功夫,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任谁也不能接受。
王立趁那女子抬手拭泪的时候,解开那她放在几案上的革囊,只见里面盛着一个血迹斑斑、龇牙咧嘴的人头。
此情此景,着实骇人,猝不及防的王立,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那女子擦干眼泪,红着眼睛,微微一笑:
「不要多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同你没有关系!」
王立脸上一红,正要开口,却见这平日里举动如弱柳扶风的女子,提起装着人头的革囊走出房门,越墙而去。
来如飞鸟,去如绝弦。
王立想开门出去送她,早已经来不及了,他站在风凉露重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夜空。
那个两年来与他同床共枕的女人,他那牙牙学语的孩子的母亲,竟然有如此的身手!
原来,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了解过她。
夜风习习,王立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徘徊,他脚步颠踬,心如乱麻,脑子里仿佛堵了一团丝絮,怎么理也理不清。
她走了!她走了!她就这样走了!
那般的决绝。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心里,好像被凿子凿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有风呼呼地穿过,绝望地疼痛。
走着走着,耳朵里听到院门旁边似乎有响动。明知道她这一去,不会再来,他还是欣喜地狂奔过去。
门开了,她竟然真的站在门前,就象是一个梦。王立欣喜若狂。
她却避免与他的目光接触,只淡淡地道:
「从此以后,我与孩子就将天各一方,让我再喂他一次奶吧!」
王立从门前让开,妇人走进内室。他听见,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发出咯咯的笑声。他听见,女人的嘴里轻轻地哼着好听的歌谣。……看在孩子的份上,她会留下来吧。他想。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那女子便从内室走了出来,她对王立挥了挥手,便又消失在暗沉沉的夜色里。
这次,是真的永诀。可是,他还在等待,希望奇迹再次出现。
王立在庭前怅然良久,任夜晚的露水打湿了衣襟。他的头脑昏昏沉沉,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在门前站了不知有多久,他忽然想起来,好长时间没听到婴儿哭了。往常的夜里,每隔一阵子,孩子便会哭闹着吃奶。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走进屋子,点亮灯火,掀起床上的帷帐。眼前的一幕,令他差点当场昏厥过去。
小小的婴儿,早已身首异处。
那个女人,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他跌坐在床头,抚摸着孩子的尸体,放声痛哭。
他曾经视若珍宝的一切,一夕之间,没有任何预兆地,就这么风流云散了。
上天为什么如此残忍。
天色渐渐亮了,新的一天,新的希望。可是,此时此刻,王立心如死灰。
白天,对他来说,不过是痛苦的延续。新的痛苦,新的折磨,无穷无已。
坐了不知道有多久,他终于打点起精神,用一口箱子,把孩子的尸体装起来埋了。
担心仇家找上门来,第二天,他便变卖了财产,买了马和仆人,搬到附近的县里居住去了。……他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屋子里的一切,都令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旧时光。
他在等待,等待一个结果。那女子夤夜杀人,盛头以归,官府一定会派人追查吧。
到时候,他一定要当面问问,为什么她要毁了他的生活,毁了他的一切。
等了很久,也没有什么音讯。
那女子如同一滴水,溶入大海,再也看不到踪迹。
你如何在苍茫的大海中,寻找一滴水呢?
这年年底,王立便被朝廷授了官,他卖掉了宅第,前去赴任。
也许,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
故事讲完了。
不难看出,《集异记》中的这个女子,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女侠。
她隐居在市井当中,伺机发动,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机会,将仇人手刃于刀下,并砍下头颅,装在革囊里。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能够使一个女子,怀着切齿的痛恨,隐忍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她的出现,与她的消失一样,都是那么突然。
她的身影,如同流星一般,拖着幽蓝的光影,滑过夜丛,融入唐朝的暗夜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中、晚唐时期,是一个侠风盛烈的时代。政府公信力缺失,贪污腐败横行,官府不再为小民伸张正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渴望侠,也呼唤侠的出现。
唐传奇里,有很多描写侠者的故事。就连当时的大诗人,李白同杜甫,也不吝笔墨,写出了许多传之后世的篇章。
杜甫《遣怀》中写到:「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由此可见,在唐代,这种快意恩仇的任侠行为,是很为人们拍手称快的。
而一代诗仙李白本人,除了在《侠客行》中有「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诗句之外,据说他本人在年少时便有结客报仇的任侠之举。
象王立所遇见的女侠一样,报仇以后,杀子别夫,在唐传奇中亦所在多有。
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你自己隐遁便是,为什么痛下杀手,杀掉自己的孩子呢?
或者携子而去,或者把孩子留给丈夫,这两种,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女子本人,身手已属上乘,为了报仇,还等待了那么久,那么仇家的实力,定然不容小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杀止杀,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你若种下仇恨的种子,便只能滋生出仇恨的根芽。所以,女子报仇之后,必须迅速远引,否则,仇家会找上门来。
带上一个呀呀学语的婴儿,以后的路途,必然危机四伏,并增加许多危险和不确定性。
留给丈夫,若寻仇的找来,作为一个身无长技的寻常男人,自身尚且难保,又如何把孩子平安带大。
她处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
动物世界上说,母狮子遇到危险时,会把小狮子撕碎,吞到肚子里。……这是她保护自己幼崽的方式。
与其在别人手里辗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如自己下手。
了断一个鲜活的生命,也了却一切扯不断,理还乱的牵挂。
女侠未必没有真感情,只是她人在江湖行,便得行江湖事。
江湖是什么?
江湖是歌,是酒,是诗;是刀,是剑,是血;更是伤痛,是别离,是死亡,是一切残忍的,酷烈的的东西。
江湖很大,没有尽头,你可以在里面仗剑纵酒,任意遨游;江湖又很小,充斥着鲜血与屠戮,生离与死别,却容不下一个母亲的心,和一颗悲悯的泪。
唐余干县厨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倘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阽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缺。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惶惶,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萦。」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买仆」原作「仆买」,据明抄本改)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yù)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出《集异记》)
变
即便是不怎么喜欢历史的人,也知道,李德裕是唐朝人,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其中的一方「李党」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世家,少年时代意气颇高。他的父亲李吉甫曾任宪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本人,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两度为相。人生的航船,经历过急流与险滩,也曾饱览那些波涛壮阔的画面。宦海沉浮,仕途上起起落落,或者说是大起大落。他在政治上的作为,与中、晚唐的政局息息相关。而国家的治乱兴衰,也影响着他本人命运的走向。
根据他的仕官履历,我们知道,李德裕曾经两次出任浙西节度使。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就是在他出镇浙西时的经历。
李德裕出镇浙西的时候,甘露寺管事的和尚前来告状,说是寺院里的财物被以前主事的僧人私自挪用,黄金少了若干两。前几任管事的和尚卸任时,都有交接文书,写得明明白白。到他这里,就少了许多,寺院里的僧人都说是他这个新上任的给贪污了,这真是莫大的冤枉。
又说:「我要接管此事时,交接文书上各种物品的种类、成色、数量都记得十分明确,可是,等到交接那一天,却根本就不见金子!这里面大有古怪,因此到节度使这里告状,请求李大人予以裁夺。」
寺庙里的财产不少,除了做功德以外,危急时刻,也用来赈济穷乏。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隐没寺院的财产。接到管事僧人的诉状以后,李德裕命手下马上立案侦查。
案情很清楚,原来管事的和尚在强大的事实面前,甘愿服罪。但是查来查去,也没弄清楚,那笔钱究竟花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僧人不守戒规,偷着溜出去花天酒地,那些金钱,全都这么浪掷了。众口喧喧,和尚没有办法洗脱自己的罪责,只能伸着脖子等死。
终审判决那一天,李德裕总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弄清楚的地方,人命关天,不能潦草行事。他叫人把和尚押来,要亲自同他谈谈。
李德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和尚左思右想,终于据实相告。
原来,寺院里的和尚都愿意管事,此前主事的那些和尚,都在账簿上注明寺里有财物若干,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下来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金子。这件事人人心知肚明,谁也不去点破。众人因为这个和尚性情孤高,不杂流俗,为了排挤他,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
说完之后,和尚不能自已,泪流披面。
李德裕对这僧人很是同情,安慰他说:
「这是飞来横祸,谁能预料得到呢?」
一听这话,和尚一直压抑着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痛哭失声。
沉吟了一会儿,李德裕说:
「我知道怎么办了!」
回过头来叫人准备数乘软轿,叫那些与此案有关的僧人前来对质。和尚们来到节度使大堂以后,李德裕让他们全走坐进软轿,落下轿帘,彼此之间谁也看不见谁。然后叫这些人用黄泥把经手交接过的金子的模型捏出来。和尚们根本就没见过金子,当然不知道金子的大小、形状。在轿子里面磨蹭了半天,也没捏出个样子出来。
李德裕大怒,命人审问前几任主事的和尚,这些人迫不得已,一一认了罪。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些和尚心里不知道有多懊恼。
而那个受到排挤的和尚,终于得到了昭雪。
要不是节度使大人明察秋毫,他早已身首异处,成为游荡在幽冥见的一个鬼魂了。而且还是一个冤死鬼。
(出《桂苑从谈》)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佛门本是清静之地,现在看来并不清净,……世俗的纷争在这里一样也不少。
俗世中充斥的各种欲望、纷竞、倾轧、算计,这里也有。
为了一些无法摆到台面上去的原因,这些人不惜对自己的同门下手,下死手!
许多人抛弃妻子,离情绝俗,遁入空门,以为就能获得大解脱。可是最后,看他们得到了什么?
你若不慎卷入纷争,可能最终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甘露寺的和尚受人污蔑,却甘愿领罪,因为他了解寺院里的潜规则。众口喧喧,他如何能够逃脱。
遇见李德裕,对他而言,堪称幸事。从有关记载来看,这两个人似乎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桂苑丛谈》里有这样一则轶闻。说是润州甘露寺有个僧人道行很高,李德裕巡行江左的时候,还曾经与他结伴同游,饱览江左的名山大川。
寺庙里的和尚多了,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就是前面被冤枉的那一个呢?文中在描述这个僧人时,有「孤高」二字。甘露寺的和尚,又性情孤高,十有八九就是我们上面提过的那个了。
李德裕与这个僧人交情很好,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断案时结下来的吧!
卸任还京的时候,将一根方竹杖赠给他留作纪念。这根竹杖产自大宛,质地坚实,截面呈正方形,节、眼、须、牙相对而生,是李德裕非常珍爱的一样东西。
二人依依惜别。数年以后,因缘际会,李德裕再次出镇浙右,派人前去探问,僧人竟还健在。
见面之后,百感交集,闲话了一会儿之后,李公问道:
「此前我送给大师的那根竹杖还在吗?」
「在!在!」僧人一迭声地答道。「老衲已经命人将它削圆,并且漆上一层清漆了!」
李德裕听了,当时不动声色。回去之后,感慨惋惜了一整天。
《桂苑丛谈》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寥寥数语,但是,似乎暗含着某种隐喻。
竹子都是圆的,方形的竹杖,一定是非常稀有的吧。
就如僧人当年,孤傲清高,头角峥嵘,不同于流俗。在那些面目平庸,拉帮结派的同门之间,是如此的特出。以至于,那些人无法改变他,便想要他的命!
有一个异类在身边,不会有人觉得舒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那么,就削平他身上的棱角,或者,干脆除掉。
因为李德裕的干预,他们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
可是,连刀剑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岁月却能改变。
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僧人身上的棱角,早已经磨平了吧。也许,他早已认识到,自己的坚持,不过是以卵击石。他改变不了什么,那么,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自己好过点儿。
他在时间与世俗的磨砺下,渐渐变得浑圆。他不再是危险的异类,他渐渐认同了那些人的价值判断。就如同,竹子都是圆的,那么,方形的竹杖就不应该存在。
假如,竹杖是方形的,那么,就用外力将它削圆。
现在的僧人,假若遇上当年的自己,还会认识吗?他会同其他僧人一样,认为这个同门不合时宜吧!也许,在那些出头做伪证,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僧人当中,也会有他一个!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别让岁月改变你!」
可是,又有几人一意坚持当初的理想,不被岁月改变呢!
李德裕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引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杂洽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咸原作成,据唐语林改)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挥(挥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门下(下学原阙,据唐语林补)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样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出《桂苑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