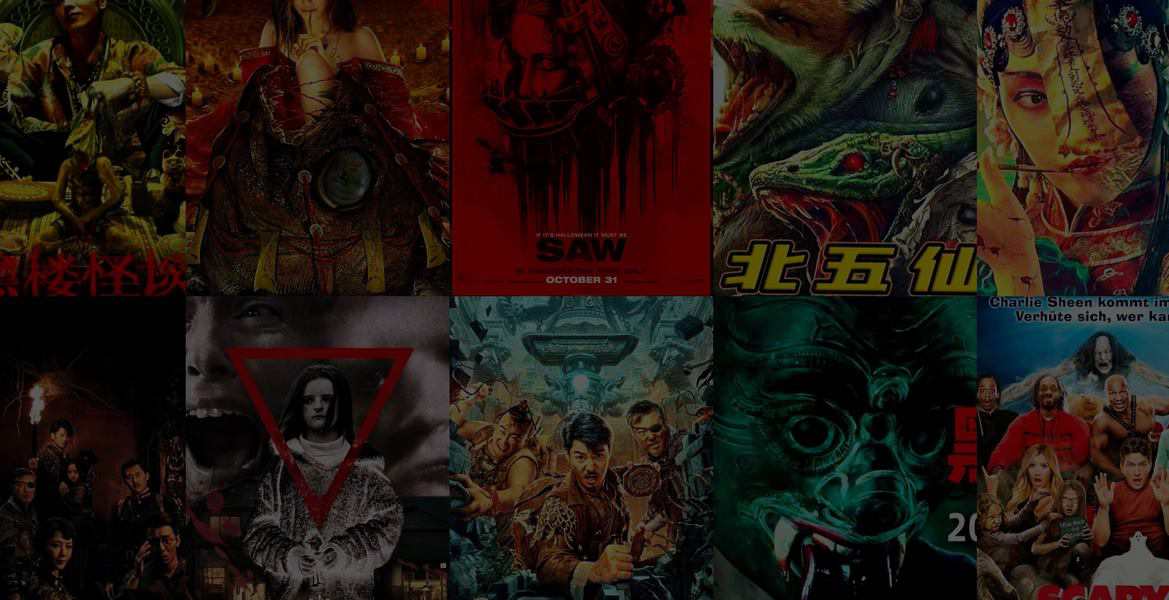鬼话连篇网-打造丰富多彩的鬼故事分享平台,这里可以体验原创鬼故事,经典恐怖小说,恐怖电影资源下载等栏目
鬼话连篇网是一个专注于恐怖文化内容的分享平台,诞生于对恐怖故事最纯粹的热爱,我们相信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都值得被讲述。这里不是简单的鬼故事聚合地,而是一个让恐怖想象力自由生长的创作家园。
侏儒
我叫魏宇,是个程序员,平日里居家工作,偶尔项目做完才会出去走走溜达溜达,我现在的公司离我家距离比较远,所以老板这才批准我可以居家工作。谁呀我敲了敲她家的门,这时从门后传来了一个老者的声音。
通州怪谈之梦游奇遇
欢迎收看老墨鬼话,我是老墨,这次老墨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绝对真实,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当事人王沐到这里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详情。哈喽,你们好,我叫王沐,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之前呢,有接待过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女孩儿,我们俩人的关系还算是不错,而且她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经常会跟我说点奇怪的故事。原本是抬眼地看着面前的镜头,不久,随着话语徐徐展开,她的眼神变得飘忽不定,好像陷入了回忆。
停尸间
寓言故事纯属虚构,无不良影响。夜深如墨,静谧无风,殡仪馆昏暗处,停尸间大门之外,有男子跪在门前不住磕头。其双膝如钉,牢牢钉于台前石板,磨损处暗红染污,竟不知是跪了多久。其上半身如摆锤摇晃,频率力道,又似鸡啄粟米,持久不停。即便已满头是血,然其仍未觉有痛,只一味砰砰磕头,同时口中含糊,既像是呓语,又像是在求饶认错。其行状诡异,似机械无休无止。
短篇鬼故事《邻居》
司徒信习惯了凌晨4点回家,却总在此时撞见503室的神秘女人。她为何永远避开白天?邻居讳莫如深的警告、5年前的分尸悬案、深夜柜中凝视的人头……当他终于敲开那扇门,才发现真相早已被砌进墙里。这是一栋吞噬秘密的老公寓,每个转角都藏着比死亡更冰冷的寒意。
短篇鬼故事《巧遇阎王》
她天生九阴之体,能见鬼魂却无力自保。一次潭柘寺奇遇,阎王亲赐阴阳眼全开,从此公交车、校园、宿舍楼……灵体密密麻麻如早高峰地铁!同学以为她疯了,她却发现宿舍楼竟成“灵体禁区”?今夜鬼节,雨夜抓鬼计划启动——但法力呢?阎王你是不是忘了给技能包啊!
短篇鬼故事《女高怪谈》
一座荒废多年的教学楼被改为高三宿舍,却接连发生诡异死亡事件。哭声回荡的深夜阳台、上吊自杀的播音员、离奇燃烧的广播室……真相背后,竟是一场因校园欺凌而引发的血腥复仇。她伪装成好友,步步为营,最终将仇人拖入地狱。但秘密从未被彻底埋葬——下一本日记的发现者,能否逃脱死亡的诅咒?
短篇鬼故事《她回来了》
2011年深夜,林小吉接到诡异电话:“我想见你”。当他回房就寝,竟在黑暗中摸到一具冰冷女尸!发小杰闻讯赶来探查,次日却离奇惨死在卧室。随着警方调查,三年前林小吉女友被杰毁容杀害的真相浮出水面。当所有人认定林小吉是凶手时,墙角毁容女人的冷笑却揭示:血债终需血偿…
探灵实录
寓言故事,本故事纯属虚构,无不良影响!斜月高悬,树影凄凄,一位探灵博主,邀请了一位资历深厚的佛学居士,共同直播探险一座荒废已久的寺庙。 两人迎着深夜寒风,站在庙门前,举着高功率手电筒,将庙门前照得亮如白昼。但即便如此光明,也未驱散博主心中的恐惧。但见那山门中央,空门破了个大洞,像是一个被砸掉了门牙的嘴。
神算老爸的离奇人生
讲述我那位看似坑蒙拐骗的算命老爸不为人知的一面。母亲命带“克夫”,右肩神秘掌印皮肤病遇见父亲后才发作;父亲三十岁“四毒俱全”却凭厚脸皮娶到她。十年间,我亲眼见证两件奇事:父亲精准预言陌生夫妻得子及孩子的“水劫”,多年后获重谢;更惊悚的是,陈大爷去世当夜,其亡魂竟登门与父亲把酒长谈,而我险些被其触碰!父亲的神秘规矩与紧张护犊,揭示他或许真能窥见阴阳。这是一个关于看似不靠谱的父亲、奇特父母爱情与背后玄妙力量的家庭秘闻。
短篇鬼故事:恐怖陵园招聘
失业青年王虎为生存所迫,应聘西山陵园的高薪守夜职位。诡异面试层层筛选:信不信鬼?午夜独自入园寻灯!顶着恐惧深入密密麻麻的坟茔,王虎在乱葬岗旧址终于找到目标——却撞见妖艳的林秘书正生啃另外两名应聘者的血肉!千钧一发,神秘老人所赠的麻线小人显灵挡灾。王虎亡命奔逃,好不容易拦下出租车,司机嘶哑的嗓音和缓缓转过的脸...让他彻底坠入深渊。高薪背后,竟是精心设计的恐怖陷阱?生存的挣扎,直面比鬼魂更骇人的真实恐怖。
大堂哥亲历:九十年代龙头山盗墓惊魂
九十年代初,一伙伪装成采药人的盗墓贼潜入湖北山村龙头山,借住在大堂哥家。心怀好奇的大堂哥尾随其后,亲眼目睹这伙人用炸药炸开古墓石门。墓中石棺套铜棺,棺盖将启之际,棺内竟传出抓挠声!铜棺盖猛然飞起,一身披盔甲、眼冒红光的僵尸破棺而出,以恐怖力量瞬间屠戮众人,惨叫连连、血肉横飞!躲在洞口的大堂哥魂飞魄散,眼见石像意外封死洞口,更目睹僵尸狂暴杀戮,仅凭一丝缝隙侥幸逃生。多年后,龙头山草木依旧,但那血腥一夜成为大堂哥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低声告诫:古墓里的东西,千万别碰!原因,你懂的!
七旬老人亲历诡异往事
湖北山村七旬老人德旺亲历诡异往事:五十年代深夜赶路,身后突现诡异脚步声,竟是一根成精棺材杠子作祟!青年德旺咬破中指以阳血镇压,杠子显形;后为内山坳云发看守邪门炭窑余家湾,寒夜炖肉独酌时,遭遇披蓑衣、露獠牙的树桩精怪索食,德旺眼疾手快,抄起烧红的火钳直捅怪嘴!凄厉惨叫响彻山林,天亮循声挖出血流树桩... 听老辈人讲古,揭秘深山老林里那些不为人知的精怪传说,胆小勿入!
野花莫乱采,小心艳遇变鬼妻
乡里恶霸梁蒙,好吃懒做、欺男霸女,三十岁还打光棍。一日傍晚垂头丧气回家,竟撞见个娇羞貌美的绿衣姑娘“春燕”!梁蒙贼心顿起,殷勤送“姑娘”回山头的白砖房。“岳母”热情留宿,摆上丰盛冷宴,还当晚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洞房花烛,颠鸾倒凤好不快活。美梦正酣,天亮惊醒——哪有什么白房娇妻?怀抱冰凉树根,身处乱葬岗中!供品腐坏生蛆,白碑赫然刻着“杨氏小女春燕”,镶嵌的画像正是昨夜“新娘”!梁蒙当场吓晕。老话怎讲?野花莫乱采,小心艳遇变鬼妻!
枫林村孽债,虐兽少年招来狐妖索命
长途车上,老木匠讲起一桩亲历怪事:那年雨夜赶工枫林村,湿滑山路遇一不打伞的青衣女子,雨水不沾衣、踏泥不留痕!惊魂未定到雇主家,才知雇主儿子庆生虐杀成性,如今被“狐妖”缠身,形销骨立!请道士无门,木匠提醒求告土地。夫妇雨中血叩土地庙,当夜雷声炸响,只听房内女子厉喝:“畜生敢在我眼皮下作恶!”次日见灰狐毙命,庆生虽醒却成废人。夫妻同梦青衣女道破天机:虐兽招祸本该死,念你诚心求土地,我(土地婆)才出手灭狐妖!木匠叹道:那雨中无痕女,正是显灵的土地婆婆啊!
拾粪王大爷乱坟岗奇遇
天不亮,拾粪的王大爷就摸黑赶往小河边,必经的乱坟岗阴风阵阵他也不怵。谁知快走出坟地时,一个飘忽不定的声音缠上了他:“拾粪的老头,我门前有一泡狗粪,你拾走吧!”那声音忽东忽西,瘆得王大爷魂飞魄散,粪筐子都不要了,撒腿就跑!天亮壮胆回去捡筐,竟真在一座老坟前发现一泡臭狗粪——原来夜里是坟里的鬼魂在求救!王大爷心善,顺手清理了。后来才知,狗粪克鬼,坟头有这东西,里头的鬼可遭大罪了!打那以后,王大爷过乱坟岗再没听过怪声,讲起这事,他一脸认真:“鬼求人办事,稀奇是真稀奇!”
天狗吞月夜,李二角井边撞上“狗飘子”
天狗食月夜,杀狗者闭户避祸是村里铁律。唯独狗贩子李二角不信邪,偏在血月尽蚀的漆黑之夜看守麦田水井。困倦之际,井边异响突现——一条目光凶戾的大黄狗无声飘来!李二角捡土块欲驱赶,恶犬竟四脚离地直扑面门!生死关头妻子意外现身惊散狗影,侥幸逃过一劫的李二角却在天亮后高烧学狗叫。邻村巫婆一语道破:百条枉死狗魂缠身索命!这场月蚀夜的井边惊魂,终让桀骜的杀狗贩子跪倒在禁忌之下,从此再不敢藐视天狗之怒。
雪夜撞鬼!赌徒刘二坟场惊遇白衣无影女
寒冬雪夜,赌鬼刘二独自穿越坟场归家,月光惨白下竟撞见一长发遮面、面无血色的白衣女子!擦肩瞬间,寒意刺骨——更骇人的是,女子雪地无影无痕、行走无声!生死关头,刘二急中生智点燃香烟,鬼影霎时消散。次日老支书道破真相:此乃赌鬼李坡上吊而亡的媳妇,专在月圆夜索赌徒性命!一支烟驱散索命厉鬼,这场坟场奇遇彻底吓破刘二赌胆,从此改邪归正。惊魂夜幕后,藏着怎样血泪的戒赌警示?
五岁男童惨死神秘土洞,六十年代中原老狐子索命实录
1960年代中原土山的噬童魔洞,吞噬了不听劝阻的五岁探险者。当村民彻夜挖掘四五里深洞,只见血泊中蜷缩的幼小尸身,以及一道毛茸黑影闪电般窜入夜幕——这便是代代相传专吃闹夜孩子的“老狐子”首次显形。它既非狐狸也非山魈,爪印深嵌洞壁却无兽类腥臊,唯在男童颈侧留下三道类人指痕的致命伤。从此“毛茸黑影”成为具象化梦魇,而那座被挖穿的山体裂口,至今仍在风中呜咽着未解的山精诅咒……
十二腿六眼怪猫在我童年显形了
夏夜纳凉的祖孙俩踏入月光斑驳的禁忌小树林,奶奶正要讲述专吃闹夜孩子的“三猫六个眼”传说——那怪物形似巨猫却生着十二条蜈蚣腿,脸上六只幽绿眼珠能在黑暗中锁定猎物。未等故事开场,孙儿猛然瞥见树影间匍匐着与描述完全一致的怪物!当奶奶笑称孩子被故事吓昏头时,那东西的复眼骤然在碎月下流转翡翠邪光。祖孙跌撞逃出密林后三十年,老人临终才颤声承认:那夜她分明听到身后传来幼猫哭坟般的嘶嚎……
蒜地追凶:月光下的瘸影竟是亡者预兆
三十年前满月夜,李老师撞见“瘸腿张二嫂”佝偻着偷蒜。他猛追不舍时惊觉诡谲——任他狂奔疾驰,那瘸影总保持十丈距离如影随形。喘息间隙借月光细看:人形突化作油纸伞鬼影,伞下两条细长鬼腿凌空乱蹬!当他魂飞魄退逃向村落,群犬狂吠撕破夜幕,那伞影竟调转方向反追而来,直到犬吠声将其逼回荒野深潭。黎明时分,张二嫂暴毙的噩耗传来,方知昨夜追捕的竟是新死之魂预演生前执念。
百年杨树惊魂夜:千眼白旗与幽灵掌声的三十年禁忌
三十年前闷热夏夜,五个青年闯入村口被香火供奉的百年鬼杨荫下酣睡,却在午夜被震悚奇观惊醒——树干内爆发出千人拍掌的轰鸣,每片树叶陡然睁开惨白眼眸,无数幽白旗影在枝杈间癫狂舞动!亲历教师时隔三十年讲述时仍指尖发颤:这桩被称作“杨叶拍巴掌”的中原古老禁忌,让整村人目睹精怪显形。当科学青年在古树注视下连滚带爬溃逃,那些被香火熏黑的树皮褶皱里,正渗出比夜更深的草木精魂之怒……
八旬老人亲历麦田精怪“二缸瓮”
上世纪兰考农村的诡谲阴阳夜,王大爷孤身看守麦田时遭遇百年秘闻——拇指大的黑影在麦穗疯长至缸瓮巨怪,旋又缩回消失无踪!冷风裹挟着祖辈相传的禁忌:这非妖非鬼的“二缸瓮” ,正是只在月色游移之夜现形的土地精魄。它不伤人却戏弄众生,看得见摸不着,在饥荒年代的麦浪间演绎诡诞变形记。当老人颤声揭开这段亲历奇谭,正悄然消亡的中原精怪传说,终在科学洪流中溅起最后一簇玄火……
亲历80后童年阴影“千年黑、万年白”
揭秘80后童年流传甚广却已消失的诡异存在——“千年黑、万年白”。真实讲述五岁夏夜的离奇遭遇:村东大坑边,月光下惊现一黑一白两只“兔子”。兴奋追逐间,恐怖景象上演——兔子数量诡异倍增,越追越多,直至眼前幻化出茫茫黑白两片!心惊胆战之际,猛然醒悟:这正是传说中的索命鬼兔!半月后,小树林中再次不期而遇,印证了这绝非幻觉。母亲警告:若真抓到,将化作破鞋或白布,带来不祥厄运。探索这曾真实存在于乡村月夜、形态变幻莫测、现已销声匿迹的恐怖生物,重温一代人的集体童年阴影。
鬼压身的经历
深入中国农村真实的“鬼压床”禁忌——压虎。高三少年暑假归家,于村东神庙旁的西瓜地守夜,因疏忽母亲“头朝庙墙”的避邪叮嘱,在深夜熟睡时突遭恐怖侵袭:一个透明却沉重的“东西”死死压住身体,窒息感席卷全身,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呼喊无声,甚至感觉床铺被掀立!毛骨悚然的七八分钟,仿佛与无形之物搏斗。是触怒了庙旁“不干净的东西”,还是农村流传甚广的“压虎”作祟?亲历者讲述西瓜地惊魂夜,揭开压虎的极致恐惧与母亲传授的破解之道,并探寻这普遍现象背后的科学解释。
老汉守夜遇吸血獾,童稚庙中惊鬼蝠:真实乡村异闻录
深入中国乡村的诡异夜晚,亲历两则毛骨悚然的真实异闻。王老汉半夜遭遇离奇血案:干瘪无头的母鸡,吸血遁走的“人脚獾”——一种惧成人却嗜童的恐怖生物。多年后,童年夏夜于漆黑破庙中,亲见“鬼蝠”降临,粪便如雨,沉重呼吸近在咫尺,厄运传说仿佛成真。是未知野兽作祟,还是古老禁忌中的邪灵?探索这笼罩在黑暗与民俗恐惧下的真实乡村怪谈,揭开人脚獾吸血之谜与鬼蝙蝠带来的不祥预兆。
短篇鬼故事之影子鬼
爷爷曾遇见过几次鬼,其中最让他觉得毛骨悚然,惊骇不已的就是遇见过的影子鬼。爷爷年轻时,以卖盐来维持生计。有一年八月十六,月亮又圆又大,爷爷为了赶早集占个好摊点,半夜时分就起了身,挑起盐筐子,急急地朝集市的方向赶去。
鬼故事之人脚獾
老一辈人说:人脚獾会专吃闹夜的小孩,所以在我的童年(即80后的那一代童年),若是我闹夜时,母亲总是吓唬我:孩子,你再闹,人脚獾就会吃掉你。这时我就会吓得赶紧躲进被窝里,不敢再作声。我想我们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的童年,也都是如同我一般在人脚獾的阴影下渡过的(注:它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在其它的地方也许并没有人脚獾)。然而在我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却与它不期而遇了。
短篇鬼故事:你有腿吗?
深夜,一列只有两节车厢的柴油机火车在飘着雪的刺骨寒冷的原野上奔驰着,车内只有司机和列车员两人。仅有的一个取暖用具—圆火炉烧得通红。突然一名女子叉着双腿出现在铁道上。司机立即刹车,可是已经迟了。列车把那名女子撞倒并拖出几十米才停住。她是自己跃到铁道上来自杀的。由于当时的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不可能马上通知附近的车站或立即叫警察来,所以他们决定一个人去车站,一个人留下来,通过抽签,列车员留了下来。司机走后,列车员一个人坐在车内偎着炉火刚打了个盹儿,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滋…滋…声,好象是什么东西在地上拖过的声音。列车员的脸色一下变白了。
七月十四的挡路鬼
鬼节醉闯午夜影院,一张海报引我踏入死亡剧场。前排女子反复低语“挡住你了”,在刺耳笑声中竟将自己的头颅连发拽下,蛆虫涌动的面孔滚落我膝头;后排观众五官如熟枣般纷纷脱落,售票员的尸首横陈走道。当我在烧纸婆婆的咒语中醒来,巷口路灯下站着的无面人轻声道:“麻烦让让,挡着我了”——原来鬼节的禁忌,从不让路开始。
短篇鬼故事:一张恐怖碟片引发的灵异事件
自称“恐怖片女王”的无神论者楚志静,在一家诡异碟店租到一张宣称“绝对恐怖,让你与鬼面对面”的神秘碟片。午夜观影时,家中异象频发:窗户自开、房门作响,碟片中的漩涡竟爬出恶鬼。当接到室友车祸电话赶赴医院时,她遭遇“鬼出租车”和两个“小雯”的离奇陷阱,被漆黑鬼爪扼住咽喉——那张消失的恐怖碟片,让她亲身验证了封面的死亡承诺。
红背心索命人:奶奶临终看到的“寿衣衣柜”
奶奶临终前从昏迷中诡异苏醒,向守夜的父亲描述两个穿红背心的人强逼她挑选箱中“漂亮衣服”,父亲却看不见。当护士告知隔壁病友在奶奶苏醒的同一刻猝死时,奶奶惊恐地揭示红背心是索命勾魂使者,箱中衣物实为寿衣,是父亲的呼唤暂时赶走了他们。然而一周后,奶奶仍死于心脏病,留下她是否最终“选择了衣服”的恐怖悬念。
短篇鬼故事:镜魇噬心
李医生办公室的镜中浮现狰狞鬼影,一声惨叫后,归来的“李医生”性情骤变。医院接连发生离奇失踪,人心惶惶。暗恋他的护士小郑在夜班时窥见了他对镜狞笑的恐怖一幕,被拖入黑暗。红纱蒙头,刀叉寒光,一场扭曲的“仪式”在猫叫声中戛然而止,唯留血迹斑斑。同事小雪背负自责,决心揭开挚友失踪之谜,而镜中的恶灵,正等待着下一个猎物。
永夜教室:千年吸血鬼的赎罪血痂
身为存活千年的异类,吴季民在阳光下游走于教师身份与吸血鬼本质之间,永恒的孤寂驱使他进行禁忌实验——将车祸惨死的女学生叶然转化为不惧阳光的“完美造物”。当叶然成为他扭曲的“女儿”与精神寄托时,千年前的恋人携复仇烈焰归来,宿敌围剿中,身沾汽油的他站在火场中央,必须在自我毁灭拯救叶然、与袖手旁观任其湮灭间做出抉择,而每一次对生命的亵渎,都在他古老的灵魂上刻下新的血痂。
短篇鬼故事:催命婆婆
一名避雨的游客误入死寂小镇,为求栖身谎称患病入住唯一亮灯的医院,却不知自己踏入十日必死的绝症诅咒,更在第九夜目睹神秘鬼婆索命笑靥,恐慌中他违背禁忌逃离绝地,以为劫后余生归家狂喜,却在打开电视的瞬间,屏幕映出索命阴笑,隔日暴毙引发上海沦陷,恐怖诅咒正随电波蔓延,下一个,会是你的屏幕吗?
噬魂古树:夜校七日诅咒
高考落榜的我被母亲送入济木学院,午夜列车载着四人驶向诡异终点:空荡月台、无脸教师、吞噬人影的游廊。当血月照亮校园虬枝盘绕的噬魂古树,红坎肩校服在深夜吸食学生血肉。看坟人用玉佛揭开百年诅咒——白昼即永夜,树根缠尸骨。我们必须在倒计时结束前闭眼向东狂奔,背后是撕裂夜空的吸血枯枝……
噬血蓝翼:校园索命蝶
宁静大学校园突遭诡异蓝蝶袭击,受害者瞬间化为干尸,恐怖弥漫。中文系学生阿扬深恶蝴蝶,其女友蝶却痴迷不已。当蝶在郊外神秘五芒星石阵下带回一枚蝶蛹,并在实验室孵化出幽蓝发光的美丽蝴蝶时,校园干尸案接连发生。阿扬深夜险遭蝶群毒手,幸被一位身着红风衣、能操控青色火焰的神秘女子沈夙夜所救。为追查灾难源头,沈夙夜强迫阿扬和蝶带她前往发现蝶蛹的山中禁地。在死寂的夜色里,沈夙夜凝视着用思念召唤出的、俊美非凡的古代男子“尚钺”的幻影,向震惊的阿扬吐露出一个冰冷而痛苦的真相:她亲手终结了挚爱之人的生命。噬血蓝蝶的阴影、古老的石阵秘密、沈夙夜背负的沉重过往交织在一起,一场关乎校园存亡与古老诅咒的危机悄然降临。
风水师与双水屯的未解怨咒
建筑系的风水课轻松随意,外聘讲师王风尤其擅长讲述各种风水禁忌背后的诡异传闻。最后一堂课上,他抛出一个发生在本地“双水屯”的骇人往事:1946年寒冬,外出逃荒的西水村男人们提前归来,引发恐慌。当东水村的妇人前来寻夫,一场因“鞋子”引发的血腥冲突,揭开了西水村人山中绝境下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径。惨剧发生后,西水村接连发生离奇死亡与闹鬼事件,最终化为荒村。多年过去,荒村旧址竟建成了如今这所大学。下课铃声响起,王风送上假期祝福,却独自留下,用一块油润古老的神秘罗盘测算方位,神情严峻地望向教学楼西北方那片插着“东海堂株式会社”牌子的空旷之地,仿佛那里潜藏着比故事更深的秘密,一丝寒意悄然弥漫。
湘西尸变:一个村落的僵尸瘟疫
清朝初年,湘南山村浪子成三挖出百年腐尸身中尸毒,被村民虐待致死。月黑风高夜,他挣脱绳索尸变成嗜血僵尸,一夜屠尽张老头全家。当村民持械围剿时,发现成三已成眼冒红光、力大无穷的怪物。短短数日,被咬村民接连尸变,七百人村落沦为僵尸巢穴,“尸村”恶名从此传遍湘西。
凶宅保单:枕边人的致命致幻剂
新婚妻子独守低价购入的“凶宅”,夜半敲门声、血红猫眼、窒息电话接连不断。邻居透露前房主是被丈夫掐死的冤魂。当“女鬼”长舌贴面索命时,她暗中化验丈夫递来的牛奶——竟含致幻药!原为掩盖炒股亏空,他精心制造灵异幻象,欲诱发妻子心脏病骗保。最终她在装死中听尽阴谋,用花瓶反杀枕边人,血溅婚誓。
都市惊魂夜:五个颠覆认知的致命禁忌
五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都市传说交织上演:一位沉迷“珍肝煲”的食客,最终成为老板眼中“新鲜”的原料;好奇拨通自家号码的艾琳,陷入了预知死亡的致命循环;因贪婪不断拔下“神毛”变钱的李天,最终承受了剥皮之痛;被“身后笑声”折磨的求助者,在驱逐“影子”后永远失去了快乐的能力;而四个炫耀丈夫的女人,惊觉枕边人竟是同一男子。这些故事或荒诞诡异,或细思极恐,共同揭示了潜藏在日常表象下的惊悚与人性深渊。
校园情侣的死亡诅咒:一句被禁止的“再见”引发的血案
校园情侣晓儿与大庄的爱情始于一次纯真的感动,却在毕业前夕因一句“再见”而走向诡异深渊。当晓儿厌倦了男友朴实无华的告别方式,赌气要求“创意”并禁止说“再见”后,大庄在归途遭遇惨烈车祸身亡。悲痛欲绝的晓儿随后竟遭遇已化为厉鬼的大庄驾驶摩托车索命,只因那句被剥夺的“再见”成了无法安息的执念与诅咒。
死亡游戏:民工与八十块手机的致命循环
生活拮据的民工孙A,用省吃俭用的八十元买了个只能玩俄罗斯方块的旧手机,并将其作为发泄生活怨气的工具——通过故意快速“Game Over”来获得扭曲的快感。然而,当他在工地遭遇一场宛如游戏画面重现的致命“砖块雨”后,那熟悉的“Game Over”竟成了生命终章。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策划这一切的工地老板,正是当初卖给他手机的旧货贩子,一场冷酷而循环的剥削游戏悄然重启。
康乃馨没有盛开在三月《家事》
高中女生小艾为摆脱追求者乔韦的纠缠,与其结成名义“夫妻”,却私下认篮球明星田满作“儿子”。三人形成微妙关系链:乔韦是“丈夫”,田满是“儿子”,小艾身兼“妻子”与“母亲”。当田满深夜携康乃馨拜访,与小艾在路灯下相拥时,被小艾父亲强行拆散。这场青春期角色扮演游戏,终在成人世界的介入下戛然而止。
刀子的声音
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我”在县城晚报角落发现一则离奇新闻——河流捞沙船打捞出一口装有裸体女尸的皮箱,死者面部被毁,身份成谜。出于隐秘动机,“我”藏起报纸,却被好友约至茶馆单间。好友以“讲故事”为名,娓娓道来一桩骇人往事:一对恋人因男方病态占有欲走向毁灭,男方以藏刀威胁女友社交,最终在分手前夜将其杀害并抛尸河中,更精心伪造女方留学美国的假象。随着故事细节与“我”的反应逐渐重合,好友亮出刻有“我”名字的凶器,揭露“我”即凶手,并以沉默为筹码索要报答。
杭州工厂三楼,那根浸透怨毒的棍子
2016年杭州某工厂老旧宿舍楼,一名新员工被安排入住传闻已久的三楼空房,首夜便遭遇关灯后诡异人声与哭泣,被迫开灯至天明,第二夜更经历与“人形拖把”的生死搏斗,其惊悚描述令老工友想起尘封往事:多年前,一名遭受暴力与不公对待的年轻女工,在此处用迷药放倒施暴者及其同伴,并用拖把棍将仇人勒死于厕所后服毒自尽,此后三楼便萦绕着不散的怨念与异响,成为无人敢踏足的禁忌之地。这则源自亲历者转述的故事,揭示了底层工厂的阴暗角落与怨灵不息的骇人真相。
凶手的两天
周荣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网友约会,却不知自己正踏入精心设计的死亡陷阱。当他在午夜掐死勒索他的“鱼儿笑”后,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房东老太离奇死亡,手法竟与他的作案方式一模一样。随着一张神秘照片的发现,周荣逐渐揭开真相:原来凶手就藏在他身边,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封死者留下的绝笔信......
半夜时,千万不要对着镜子梳头
深夜的图书馆里,一本消失的旧书,一张诡异的纸条:“半夜时,千万不要照着镜子梳头……” 转校生“稻草”本不信邪,直到她在午夜盥洗室撞见一个滴着血梳头的女生,而第二天,那个女生离奇死亡。更可怕的是,诅咒蔓延到了寝室——当室友君在午夜对镜梳头时,她的眼球突然变白,双手掐住了“稻草”的脖子……镜中的女鬼渴望新的替身,而“稻草”成了下一个目标。午夜12点,她的双手不受控制地拿起剪刀,剪开自己的头发,鲜血顺着发丝流淌。当镜中的倒影对她露出微笑时,她才明白:最深的怨念,藏在所有长发女孩的镜子里……
影子站着的吊死鬼:凶宅悬魂夜
城中村那间出租屋的灯泡,仿佛被厉鬼紧紧扼住咽喉,灯光忽明忽暗,挣扎闪烁。昏黄的光线将墙壁上的霉斑与污渍,投射成张牙舞爪的怪物剪影,它们在空气中无声地扭曲、蠕动。林尼站在门口,后背紧紧抵住门框,双脚如同被黄泉的淤泥死死黏住,目光呆滞地凝固在房间中央——在那里,一个女人正以极其诡异的姿态悬在半空。她墨瀑般的长发披散而下,遮住了大半张脸,仅露出的下颌线紧绷成僵硬的直线,双脚离地仅有寸许,脚尖无力地耷拉着,随着气流轻轻晃动,仿佛在无声地哭诉着什么。这是林尼咬咬牙才租下的便宜房子,当时中介拍着油光锃亮的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性价比超高,干净又敞亮。可谁能想到,搬进来的头一晚,就撞见如此阴森恐怖、渗人骨髓的场面。
嘘…卫生间隔间里的哭声别应!
我们剧组在一个废弃的旧厂区拍戏,这地方与其说是废弃,倒更像是一座被岁月与诅咒双重侵蚀的鬼楼。墙体皲裂的缝隙间,时不时渗出暗褐色的水渍,风刮过空旷的车间,发出呜呜的哭号声,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倾诉悲苦。那天收工很晚,暮色犹如一块浸满墨汁的布,沉甸甸地压下来。我突然内急,想起道具组老张曾提过,后院有间不知年代的卫生
八仙饭店
我是一名热衷于挖掘旧闻秘事的自由撰稿人,始终坚信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中,隐匿着人性最深处的黑暗。在整理老城区档案时,一张布满霉斑的黑白照片,猛地吸引了我的视线。照片里,八仙饭店的招牌半掩在铁闸门后,字体因风雨侵蚀而斑驳不堪,但八仙饭店这四个字,却如同淬了毒的咒文,在昏黄的光线中散发着难以言喻的阴森气息。照片标注的日期是1985